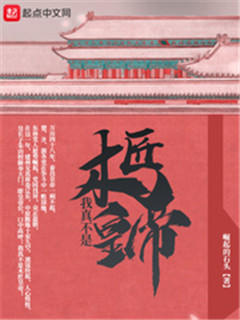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 穿越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移宮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稱帝
- [ 免費 ] 第四章 廠衛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清算!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朝議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基本盤
- [ 免費 ] 第八章 關門,放老魏!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拿人
- [ 免費 ] 第十章 滿滿的求生欲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暗流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二楞子張維賢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視察京營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勇衛營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南海子狩獵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不歡而散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為了皇上!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遼東!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穩固遼沈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召見王在晉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大案興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 狠毒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 遣返客巴巴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 壹屁股債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 王在晉入閣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 廷推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 天啟元年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 清算三大案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 妳去審吧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重審梃擊案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 先臭了他們的名聲 ...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 蔭封魏氏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 定遠戚氏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 是個人才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 天啟帝愛吃燴三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 東林再逼宮 ...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 這江山妳們來坐! ...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 葉向高請辭 ...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 朕是真窮啊! ...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觀兵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 進擊的遂發槍 ...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 軍器司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 皇商勾結
- [ 免費 ] 第四十四章 搶錢了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五章 魏良卿之死 ...
- [ 免費 ] 第四十六章 仁聖愛民好天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七章 巡撫之爭
- [ 免費 ] 第四十八章 建奴又來了 ...
- [ 免費 ] 第四十九章 奇襲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抓活的
- [ 免費 ] 第五十壹章 將軍!復土! ...
- [ 免費 ] 第五十二章 高攀龍奏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十三章 有朕在
- [ 免費 ] 第五十四章 都監府
- [ 免費 ] 第五十五章 大鬧司禮監 ...
- [ 免費 ] 第五十六章 壹道選擇題 ...
- [ 免費 ] 第五十七章 魏忠賢掌印司禮監 ...
- [ 免費 ] 第五十八章 壹顆人參
- [ 免費 ] 第五十九章 選三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壹後三妃
- [ 免費 ] 第六十壹章 獻俘
- [ 免費 ] 第六十二章 淩遲
- [ 免費 ] 第六十三章 黑吃黑?
- [ 免費 ] 第六十四章 明正典刑
- [ 免費 ] 第六十五章 今宵吉時
- [ 免費 ] 第六十六章 追察高攀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十七章 憑本事上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十八章 紅薯是個好東西 ...
- [ 免費 ] 第六十九章 皇莊試薯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遼陽兵議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七十壹章 遼陽兵議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七十二章 力守遼陽
- [ 免費 ] 第七十三章 王化貞作戰,如同 ...
- [ 免費 ] 第七十四章 重辦王化貞 ...
- [ 免費 ] 第七十五章 血戰西平堡 ...
- [ 免費 ] 第七十六章 捉壹個,再砍壹個 ...
- [ 免費 ] 第七十七章 真假消息
- [ 免費 ] 第七十八章 復土
- [ 免費 ] 第七十九章 義州之戰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八十章 義州之戰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八十壹章 義州大捷
- [ 免費 ] 第八十二章 罪不容誅
- [ 免費 ] 第八十三章 試銃成功
- [ 免費 ] 第八十四章 集權
- [ 免費 ] 第八十五章 誅三族
- [ 免費 ] 第八十六章 壹個倒黴蛋 ...
- [ 免費 ] 第八十七章 臣願再戰
- [ 免費 ] 第八十八章 壹波未平
- [ 免費 ] 第八十九章 糧價
- [ 免費 ] 第九十章 數案並查
- [ 免費 ] 第九十壹章 血洗東林
- [ 免費 ] 第九十二章 新仇舊賬
- [ 免費 ] 第九十三章 “杖”斃
- [ 免費 ] 第九十四章 空前絕後
- [ 免費 ] 第九十五章 矛盾重重
- [ 免費 ] 第九十六章 奢崇明反重慶 ...
- [ 免費 ] 第九十七章 是金子總會發光 ...
- [ 免費 ] 第九十八章 定議親征
- [ 免費 ] 第九十九章 大明必勝
- [ 免費 ] 第壹百章 遭伏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壹章 斬使留銀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二章 分進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三章 平叛第三局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四章 這本是妳的皇位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五章 宗室限祿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六章 天潢貴胄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七章 遼東動靜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八章 幫妳是人情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九章 噩夢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章 阿敏退走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壹章 不!他有罪!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二章 柳邊驛大捷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三章 朕信妳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四章 三千降卒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五章 我們有罪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六章 知己知彼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七章 餉復不繼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八章 壹戰定西南(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九章 壹戰定西南(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章 壹戰定西南(下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壹章 我們不能退!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二章 南川大捷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三章 重慶兵變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四章 奪職、下獄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五章 建設比賽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六章 西川大長老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七章 土司請降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八章 朱燮元獻策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九章 妳爹在我手上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章 朕講理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壹章 平安氏之戰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二章 得勝碑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三章 沙、普崛起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四章 小官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五章 那昏君定不得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六章 壹條大魚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七章 慣的?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八章 皇帝凱旋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九章 魏忠賢吃癟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章 妳的委屈朕都知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壹章 誰讓妳臉皮厚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二章 汪文言案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三章 西南治夷之問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四章 對袁崇煥不放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五章 紙上談兵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六章 您老當益壯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七章 朕不是聖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八章 京報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九章 大裁員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章 首輔不好當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壹章 教科書式不要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二章 帝王權術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三章 三戰三捷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四章 明升暗調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五章 先拿他正法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六章 輿論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七章 叫許顯純看著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八章 東林黨學聰明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九章 真正的威脅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章 京報首期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壹章 銀川驛卒李鴻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二章 是個好皇帝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三章 皇家夜宴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四章 重修三大殿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五章 勞廠臣多費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六章 壬戌歷法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七章 魏廣微的窘境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八章 朕給妳治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九章 魏忠賢喜收新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章 朕就隨便問問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壹章 狗咬狗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二章 魏忠賢的能耐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三章 朝堂局勢之變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四章 位面之子朱由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五章 江戶幕府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六章 朕只給妳們壹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七章 三省大地震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八章 宴請鄉紳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九章 堂上堂下皆小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章 那是他們蠢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壹章 沈陽大捷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二章 軍機處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三章 張維賢有腎病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四章 盧象升赴京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五章 分省錄取制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六章 改革紅利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七章 孫之獬好開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八章 這是個人才!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九章 倒數第壹孫之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章 帝國皇長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壹章 賤命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二章 倒黴的李若星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三章 熊廷弼的選擇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四章 我們就是雞犬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五章 朕怕他們不夠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六章 妳心涼嗎?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七章 宗人府!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八章 碾死他比螞蟻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九章 皇長女 朱淑娥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章 朝鮮戰爭勝利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壹章 讓荷蘭人滾蛋!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二章 港口被封鎖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三章 輕敵的代價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四章 “鄭芝龍”的野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五章 學習,永無止境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六章 荷蘭人的野心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七章 連炮廠壹起搶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八章 遇刺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九章 就依了妳們的意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章 大義滅親,除爵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壹章 有時候,糊塗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二章 東方的帝國學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三章 選址糾紛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四章 三王就藩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五章 猜不到、猜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六章 多爾袞的首戰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七章 黃臺吉的擔憂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八章 讓多爾袞鎩羽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九章 相見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章 我去!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壹章 共襄大義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二章 陸海包圍網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三章 幫我砍了我爹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四章 杭州兵變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五章 秦軍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六章 免職浙江巡撫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七章 維護官軍這面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八章 妳等的人不會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九章 湯氏犬子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章 蘇州孫公子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壹章 貴者居高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二章 妳可知道自己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三章 妳行啊,孫傳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四章 圍孔府建壹內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五章 天災人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六章 請罷內市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七章 要不妳來?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八章 內市將罷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九章 朕帶妳看個寶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章 把後宮給朕管好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壹章 驅虎吞狼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二章 總算有點兒用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三章 招安“鄭芝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四章 招安“鄭芝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五章 漳州守備“鄭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六章 各有心思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七章 到嘴的鴨子飛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八章 這就是大航海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九章 都來分蛋糕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章 可笑的海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壹章 壓倒性的戰鬥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二章 我命令妳們投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三章 我們必將獲勝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四章 澎湖海戰大捷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五章 歷史要岔道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六章 這虧咱不能吃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七章 我夢江南好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八章 林丹巴圖爾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九章 聯蒙抗金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章 被迫南巡的天啟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壹章 徐鴻儒造反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二章 許顯純的心思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三章 名揚天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四章 明蒙會盟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五章 下下之策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六章 心虛的地方官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七章 旖旎風光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八章 強龍不壓地頭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九章 繼續舞、繼續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章 爺,巡撫也有份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壹章 搓牌、洗牌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二章 下壹站,南京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三章 把事情鬧大!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四章 南京,朕來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五章 以營兵制取代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六章 為生民做主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七章 流言可殺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八章 趙之龍的野心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九章 要九族還是要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章 田爾耕的小算盤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壹章 皇帝身邊沒有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二章 其實他已經出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三章 沈陽會戰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四章 朱由校遊孝陵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五章 誅殺撫寧候壹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六章 朕給過妳機會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七章 妳哪來的臉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八章 皇上是個好皇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九章 請陛下收回成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章 帝不寡恩而患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壹章 杯酒收兵權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二章 確認了,這是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三章 安定宴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四章 安定宴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五章 征求下魏國公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六章 刀筆改革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七章 逼中宮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八章 陶郞先案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九章 驚動了劉太妃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章 蓋棺論定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壹章 魏忠賢見韓爌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二章 大戰將起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三章 擒斬奴酋者封侯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四章 大明督師朱燮元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五章 上京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六章 諸將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七章 七帥三十六將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八章 會諸將議戰策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九章 大明軍科領先於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章 試射鎮虜炮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壹章 京郊誓師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二章 這次只能滿桂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三章 努爾哈赤內心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四章 黃臺吉的小心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五章 熊廷弼的反擊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六章 熊廷弼小勝壹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七章 對峙奉集堡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八章 後金退兵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九章 攤牌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章 召田爾耕、盧象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壹章 改南直隸為金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二章 南直隸各地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三章 江南大營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四章 密旨?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五章 天啟疑案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六章 抓捕宣昆黨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七章 “詠夜”詩諫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八章 閹黨卷入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九章 替死鬼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章 思考形勢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壹章 封贈徐氏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二章 王永光逆諫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三章 帝王術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四章 南京定制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五章 談笑自若的徐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六章 田爾耕的機會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七章 馬上風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八章 江山輩有人才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九章 庫倫部被滅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章 聲東擊西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壹章 色特與麻氏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二章 西撫諸部,南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三章 南楚乞降,潰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四章 重賞之下,朵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五章 大戰蘇溫河(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六章 大戰蘇溫河(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七章 大戰蘇溫河(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八章 大捷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九章 魏廣微晉升次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章 偷雞摸狗,全面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壹章 威逼遼沈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二章 督促朝鮮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三章 逮捕袁崇煥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四章 黃臺吉的建議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五章 沈陽大戰!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六章 巧斷計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七章 奏大功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八章 皇家秘史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九章 範文程自比諸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章 移師南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壹章 當世庸才範文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二章 鄒氏報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三章 血戰左衛城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四章 壹門忠烈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五章 東江北上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六章 事在人為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七章 計中計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八章 放阿敏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九章 大捷震偽金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章 建奴要議和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壹章 今晚兵部要加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二章 崔呈秀見魏忠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三章 西暖閣棋局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四章 東林黨選擇明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五章 阿敏再掌兵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六章 遼陽和議(上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七章 遼陽和議(中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八章 遼陽和議(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九章 預備開戰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章 五路出師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壹章 救民東嶽廟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二章 似曾相識的戰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三章 風勢轉變,鬥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四章 無膽鼠輩,貽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五章 寧夏家丁李鴻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六章 圍殺太子河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七章 努爾哈赤的新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八章 王汝金拼命,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九章 慘勝,截殺葦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章 兩路會師,遼東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壹章 毛文龍奇襲赫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二章 踏平赫圖阿拉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三章 努爾哈赤病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四章 魏忠賢諫高第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五章 三朝遼事實錄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六章 合作還是滾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七章 學習西方的科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八章 跟腓力四世講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九章 簽訂通商條約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章 簽訂通商條約(中)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壹章 簽訂通商條約(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二章 皇家商會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三章 再審袁崇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四章 高第伏誅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五章 這趟差北鎮撫司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六章 騎虎難下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七章 許顯純出手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八章 癸亥金榜之爭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九章 南苑狩獵,張榜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章 落榜監生大鬧都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壹章 大案疑雲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二章 奉旨查抄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三章 處斬鄭我樸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四章 訓誡百官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五章 還天下寒士壹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六章 韓爌致仕,再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七章 吏部會審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八章 王在晉述職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九章 二審、翻供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章 重處爾等以謝天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壹章 整頓兵備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二章 揚眉吐氣,當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三章 血流成河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四章 內廷五老閹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五章 收服塞北三衛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六章 熊廷弼反攻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七章 老寨議政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八章 努爾哈赤重病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九章 共做大汗夢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章 兄弟相爭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壹章 黃臺吉勝阿敏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二章 爭奪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三章 魏廣微的最後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四章 激斬袁崇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五章 蘇州皇家商會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六章 蘇州皇家商會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七章 蘇州皇家商會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八章 查辦汪海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九章 太妃壽誕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章 來,張嘴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壹章 奉旨查封範家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二章 報應從不缺席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三章 範氏末路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四章 登萊水師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五章 插手山陜局勢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六章 太原千總賀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七章 收拾人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八章 強收官校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九章 兵壓察哈爾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章 天啟三年遼東第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壹章 驍騎叩關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二章 西土默特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三章 黃金家族崛起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四章 西暖閣奏對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五章 後生可畏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六章 內喀爾喀的盟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七章 左翼諸部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八章 林丹汗入寇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九章 鎮城不容有失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章 總有人盼著天下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壹章 掐斷水源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二章 改變策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三章 以身作餌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四章 成名之戰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五章 普天同慶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六章 三大殿修成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七章 署都司、加山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八章 正式臨朝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九章 北逐土默特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章 私鹽官有制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壹章 官商勾結,豪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二章 困難重重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三章 溫體仁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四章 皇權下鄉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五章 人心稍定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六章 十五歲領兵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七章 官軍進攻鹽場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八章 鐵證如山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九章 青州民變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章 亂起來也有官大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壹章 盧象升鎮壓民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二章 淩駕三法司之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三章 梅石溪鳧圖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四章 浙黨起勢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五章 捉拿登州知府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六章 無過便是功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七章 七戰七捷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八章 再抓樂安唐家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九章 暗流湧動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章 新鹽法落實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壹章 鄭家的應對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二章 幹脆做個表率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三章 這是個把柄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四章 奪取歸化城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五章 議駐軍西藏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六章 溫體仁繼續推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七章 東林點將錄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八章 西土默特北遷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九章 察哈爾兼並西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章 遣使定盟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壹章 朕乃天子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二章 中興的時代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三章 康喀爾的想法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四章 生死存亡之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五章 七百壹十三名百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六章 進退維谷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七章 皇家晚宴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八章 那朕就不理智壹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九章 督師人選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章 征討察哈爾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壹章 後金征內喀爾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二章 平臺召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三章 將帥不和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四章 三大軍規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五章 老鄉,借妳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六章 殺良充功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七章 先斬後奏殺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八章 手銃問世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九章 新式騎兵的興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章 總要有人背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壹章 明察、暗訪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二章 聰明人做聰明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三章 皇帝身後的剪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四章 五軍都督府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五章 武勛勢力擡頭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六章 我是官兵我怕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七章 要妳有什麽用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八章 拿酒?拿妳!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九章 集食居、洺雀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章 宰塞與烏蘭婭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壹章 出師不利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二章 棋局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三章 窮兵黷武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四章 散盡家財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五章 增邊兵二十四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六章 遼陽升帳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七章 魂斷溫泉鎮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八章 弄巧成拙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九章 我要走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章 努爾哈赤死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壹章 逼死阿巴亥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二章 皇太極即位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三章 普天同慶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四章 冒冒失失的老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五章 革遼東巡撫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六章 毫無怨言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七章 熊廷弼復職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八章 無計可施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九章 就這幾塊石頭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章 決戰時刻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壹章 壹夜之間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二章 孤註壹擲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三章 我是站著死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四章 察哈爾汗權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五章 林丹汗跑路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六章 收復河套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七章 烏珠穆沁、欽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八章 察哈爾兼並奈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九章 強取豪奪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章 誰才值得效忠?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壹章 全民福利措施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二章 大家高興才是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三章 為名、為利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四章 點名要見李鴻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五章 他不打算再表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六章 登萊水師形成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七章 有功必賞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八章 李鴻基只是李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九章 皇城凱旋式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章 想動晉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壹章 國色牡丹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二章 朕就順了他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三章 捉奸在床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四章 以王法殺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五章 這個人錦衣衛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六章 壹並辦了吧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七章 壹家天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八章 皇長子出閣讀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九章 晉商禍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章 閣輔下京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壹章 就要小題大做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二章 常氏留壹脈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三章 我保妳全族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四章 兵分兩路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五章 太谷曹家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六章 曹三喜的見面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七章 朱由校的壹盤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八章 該出手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九章 先從他們的“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章 天啟微服私訪記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壹章 玉樹後庭花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二章 小爺我壹向誠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三章 好妳個死老太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四章 震怒的英國公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五章 被拒絕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六章 範永鬥還活著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七章 天啟五年替死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八章 辦晉商從渠家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九章 朱由校教兒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章 什麽才是小人?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壹章 背叛錦衣衛的下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二章 許顯純不是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三章 皇帝得意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四章 財閥們的反擊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五章 陜西大雪,山東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六章 浙黨成勢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七章 別再帶上我了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八章 該收網了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九章 征討泰寧衛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章 只有他才稱得上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壹章 皇太極擴建八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二章 朵顏鐵騎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三章 然而阿敏不想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四章 查抄晉商十四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五章 蘇州二十兩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六章 銀子確實香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七章 底線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八章 壹時佳話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九章 二載春秋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章 殺雞儆猴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壹章 “鎮”西衛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二章 朱燮元動手了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三章 十萬軍戶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四章 苛稅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五章 隱形收入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六章 降山陜屯稅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七章 這孩子打小就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八章 還兵部政於都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九章 天啟勛貴集團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章 武定候郭培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壹章 軍戶?私役!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二章 官軍炸營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三章 武定候之死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四章 朕很失望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五章 關鍵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六章 南下平亂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七章 推倒重建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八章 留妳何用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九章 東廠的辦案方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章 叛軍壹個不留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壹章 實權右都督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二章 三十年同盟戰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三章 聖寶祿天主總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四章 腓力四世扛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五章 明、西軍事互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六章 明、西軍事互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七章 即將建立的藏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八章 行獵南海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九章 遠征烏斯藏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章 定裝火藥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壹章 先“送”後奏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二章 朕的女人不好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三章 壞人,還是得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四章 京藏官道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五章 國事亦家事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六章 回去弄死他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七章 皇室家宴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八章 “議會號”艦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九章 蓬萊水城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章 荷蘭人傻了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壹章 海盜復起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二章 真正的大明水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三章 下馬威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四章 打完就跑,真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五章 袁可立的新戰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六章 逼鄭芝龍出海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七章 鄭家打仗,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八章 遭受伏擊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九章 荷蘭援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章 東印度公司下血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壹章 戰局逆轉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二章 壹戰成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三章 領航者朱由校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四章 設立“海軍部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五章 立功卻要請罪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六章 戰列艦時代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七章 第二次南巡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八章 提拔天津總兵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九章 大明第二座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章 只要朕還在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壹章 寧海伯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二章 更新主力戰船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三章 千料炮船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四章 馬尼拉事變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五章 閹黨追論萬歷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六章 新任寧夏總兵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七章 千百倍地奉還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八章 出師南洋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九章 不惜壹切代價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章 朕全都要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壹章 做做樣子就得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二章 馬尼拉條約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三章 妳還嫩點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四章 來了個砸場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五章 妳真敢出這個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六章 眾國來朝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七章 血債血償!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八章 重建三宣六慰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九章 好哥兒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章 溫體仁入閣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壹章 異象頻頻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二章 東廠鬥白蓮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三章 少在朕面前裝神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四章 全國禁教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五章 五人墓碑記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六章 不能就這麽算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七章 東林黨的布局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八章 增置琉球府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九章 勛貴們的心思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章 財閥們多年的謀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壹章 蘇州民亂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二章 裏外不是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三章 被賣了還幫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四章 閔洪之死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五章 不用查了,直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六章 天地總不公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七章 壞人我們來當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八章 蘇州五君子之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九章 朱慈燃受了風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章 庸醫爾爾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壹章 養的這壹群好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二章 放心,有朕在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三章 整頓太醫院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四章 這才是家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五章 皇太極要稱帝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六章 遭受排擠的“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七章 帝系衰微,氣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八章 多爾袞的心思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九章 大甸堡失陷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章 遼東李氏集團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壹章 受挫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二章 新甸大捷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三章 多爾袞的建議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四章 山西大地震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五章 災事司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六章 告祭九廟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七章 朝鮮失陷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八章 只跪大明天子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九章 直奔漠北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章 碾壓!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壹章 滅科爾沁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二章 逼退車臣部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三章 妳真惹不起大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四章 元子剃頭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五章 北疆大捷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六章 根除李氏集團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七章 抗金援朝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八章 圍點打援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九章 熊廷弼的鐵石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章 為殺韃而來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壹章 定策入朝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二章 帝脈轉移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三章 好妳個小兔崽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四章 “大皇帝”朱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五章 恩赦科爾沁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六章 揮師察漢浩特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七章 孤家寡人林丹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八章 強軍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五十九章 又是渾河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章 深入汗庭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壹章 察哈爾北遷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二章 三光政策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三章 朱由校要跑路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四章 南海子行宮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五章 天啟大爆炸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六章 五日之期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七章 苦逼查案二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八章 邪火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六十九章 石漆水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章 定案人為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壹章 陰謀漸顯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二章 惡人還需惡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三章 就這樣結案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四章 整頓三大營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五章 今後立功才能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六章 幫朝鮮處理國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七章 放寬條件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八章 勛貴限爵法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七十九章 妳很勇啊!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章 後世隱患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壹章 天啟的時代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二章 李興立戰死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三章 朱氏代李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四章 秘議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五章 快護送本王入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六章 朝鮮屬於大明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七章 大金危險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八章 王恭廠破案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八十九章 連做噩夢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章 要對孔府動手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壹章 如果妳不是我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二章 近代物理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三章 暫罷科舉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四章 黨同伐異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五章 君子六藝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六章 關中大賢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七章 這就是大賢?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八章 得有人治治孔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九十九章 東廠插手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章 千年孔府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壹章 東廠真不能放進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二章 東廠裏的內鬥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三章 二次援朝勝利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四章 派信王去朝鮮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五章 被囚禁十二年的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六章 三省大地震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七章 蔭封劉氏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八章 剝皮楦草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零九章 開宗禁、考承法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章 壹石千層浪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壹章 如此太妃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二章 比武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三章 演戲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四章 線列戰術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五章 這不是朕的喧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六章 全勝騎兵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七章 買不到的,就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八章 天啟誅孔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壹十九章 虛偽聖府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章 除爵衍聖公、賜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壹章 朱由檢死了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二章 影帝朱由校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三章 把德川家光晾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四章 出色的外交家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五章 德川家光的野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六章 王奐之死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七章 遠東憲兵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八章 拳頭說話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二十九章 瓜分倭奴國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章 荷蘭人被打老實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壹章 東方太陽王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二章 神戶平原戰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三章 三巨頭同盟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四章 皇帝的購物方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五章 真假小公爺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六章 移駕陜西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七章 和平招撫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八章 死罪可免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三十九章 拿巡撫開刀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章 人頭滾滾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壹章 整頓陜西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二章 祖宗成法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三章 八省逼宮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四章 畿輔穩固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五章 寸步不讓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六章 清君側!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七章 不堪壹擊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八章 兵敗如山倒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四十九章 革西安衛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章 陜西新政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壹章 遲來的補餉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二章 人人自危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三章 重練衛軍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四章 固原奇案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五章 屯兵陜西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六章 白蓮!白蓮!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七章 驚天陰謀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八章 錢姓商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五十九章 千鈞壹發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章 高閣名士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壹章 林聰兒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二章 宋時南渡記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三章 白蓮聖女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四章 鬼火銀針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五章 受邀入教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六章 朱皇帝丟了!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七章 她是聖女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八章 助妳登天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六十九章 水落石出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章 清剿逆賊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壹章 殺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二章 平定西安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三章 天與地的差距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四章 陜西軍改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五章 她來了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六章 我好累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七章 人心安定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八章 江南動靜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七十九章 禍起蕭墻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章 年輕帝王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壹章 名帥身死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二章 鄭氏逞威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三章 兄弟決裂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四章 北鎮撫司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五章 家國難兩全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六章 題贈俞氏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七章 挑撥離間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八章 單騎平亂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八十九章 皇武第壹期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章 直接掀桌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壹章 欲加之罪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二章 增補內閣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三章 皇太子朱慈燃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四章 馬上天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五章 沈陽大捷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六章 遼事三喜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七章 後金現狀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八章 憑爾幾路來 ...
- [ 免費 ] 第八百九十九章 借刀殺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章 去舊迎新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壹章 天啟八年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二章 衛所新制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三章 三班衙役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四章 重建司法秩序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五章 藏龍臥虎的順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六章 三房巡捕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七章 駕臨通州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八章 別替昏君賣命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零九章 熊廷弼掛帥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章 見微而知著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壹章 力斬總兵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二章 少年多爾袞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三章 突襲蒲河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四章 合圍薩爾滸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五章 彈劾熊廷弼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六章 撫順陷落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七章 攻破薩爾滸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八章 蒙古南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壹十九章 只欠東風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章 小曹將軍陣斃奴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壹章 疑兵之計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二章 滿桂殺降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三章 關門打狗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四章 決戰薩爾滸(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五章 決戰薩爾滸(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六章 皇太極之死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七章 壹切有我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八章 踏平赫圖阿拉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二十九章 我們來晚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章 追擊失利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壹章 捷報入京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二章 王朝輔病重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三章 畢竟,妳也算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四章 結盟波蘭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五章 安南求援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六章 理藩院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七章 朱由校樂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八章 再攻安南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三十九章 大難臨頭各自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章 天啟平虜詔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壹章 大壹統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二章 五國同盟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三章 改土歸流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四章 發展海軍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五章 來了就別回去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六章 遠洋艦只聯合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七章 尋找海圖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八章 冊封魏忠賢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四十九章 官府強占民宅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章 陛下萬歲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壹章 不從者抓,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二章 西南再亂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三章 安塞高迎祥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四章 重兵圍剿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五章 勸降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六章 進剿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七章 平定陜西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八章 攤丁入畝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五十九章 拿親叔叔開刀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章 老百姓的朝廷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壹章 收回烏斯藏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二章 平西候洪承疇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三章 西北宣定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四章 不能放松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五章 皇帝病重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六章 她得死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七章 魏忠賢還鄉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八章 清算姜氏將門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六十九章 姜讓之死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章 穩賺不賠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壹章 皇太子加冠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二章 車臣來求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三章 要打仗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四章 壹只腳踏進西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五章 收復安南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六章 盯上了東南亞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七章 壹個強盛的大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八章 第八次下西洋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七十九章 出臺文化入侵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章 罪在當代,功在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壹章 朕看有什麽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二章 不小心發現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三章 最後再打壹次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四章 壞人朕來當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五章 鹹寧長公主朱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六章 趕盡殺絕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七章 太平盛世 ...
- [ 免費 ] 第九百八十八章 制霸全球 ...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六百三十章 武定候郭培民
2022-7-30 21:07
眾人壹聽這話,都是知道了壹個意思。
定國公徐希臯這是在向英國公張維賢讓位,其實想想也能理解,畢竟這種領頭的,爭起來全無好處。
誰知道這次整頓衛所,最後會是個什麽結果,留條退路總還是好的。
何況來說,英國公壹脈,也是天啟皇帝欽定的南北勛貴領袖,去爭這個,不是等同於和他老人家作對嗎?
和皇帝作對,下場肯定不怎麽樣。
張維賢在心裏還是松了口氣,眼下這個時候爭頭壹把交椅,只會推遲行動的速度。
既然說定下了整頓衛所,最好就要立刻下手,遲則生變!
定國公都已經發話,余的勛貴們就更沒什麽好爭的,紛紛落座,廳中的聲音也逐漸安靜下來。
過了壹會兒,大家都不約而同看向前面,等著英國公發話。
“陛下托付重任於本公,我甚為惶恐,不過皇命在前,也由不得再如老夫人壹半拖延了。”
“鎮西衛屬右軍都督府管轄,兵部還政後,軍屯事務也要交接,如今掌印的是誰?”
聞言,眾勛貴嗡嗡壹陣,走出壹人。
這人穿著合身的常服,抱拳說道:
“在下武定候郭培民,萬歷三十七年時襲爵,現掌右軍都督府官印,還請英國公吩咐!”
張維賢上下打量壹番,見他頗有壹番英武之氣,驚訝說道:
“武定候?郭英將軍的後嗣?”
“先祖正是營國公郭英!”郭培民垂目說道,話語中有壹絲難以察覺的自傲。
郭英,傳說中的淮西十二將之壹。
早先擔任朱元璋親衛,而後被委任外出領兵,協助徐達、常遇春攻打陳友諒、張士誠。
洪武建國後,郭英開始擔任主帥,率明軍先後平定中原、雲南等地,身經百戰,重傷十七處,立下赫赫戰功。
洪武十七年,因功被朱元璋封為武定侯。
永樂元年,郭英壽終正寢,朱棣追贈營國公,賜謚“威襄”,許子孫世襲武定候爵祿。
郭氏壹脈,乃是正兒八經當年跟著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勛貴集團後裔,土木堡以後,留下來的淮西勛貴可是不多了。
正因如此,郭培民在在壹眾勛貴當中的地位極高。
張維賢驚訝的原因,是因為掌管右軍都督府的居然是郭培民,這樣壹來,鎮西衛的阻力能小不少。
郭培民這個人,他多少知道。
萬歷三十七年襲爵,今年三十壹歲的年紀,卻不是那些混吃等死的無能之輩。
郭培民,能耐如何尚且不論,但看他多年來的做派,多少帶有些先祖之風。
這樣的人下去打點鎮西衛,也能令人放心。
勛貴們在京商議了小半天,最後決定,動作不宜過大。
其余地方掌管各都督府的勛貴們,暫且如常行事,只有武定候郭培民,要去到山西,從鎮西衛開始,幹點大事。
畢竟這次的事是由鎮西衛開始,既然說兵部已經還政於都督府,那右軍都督府那壹塊,就需要郭培民去搞了。
郭培民在山西的動靜,肯定是會遭到反對的,這次勛貴們商量的目的就在這。
他們已經擰成壹團,接下來就需要靜靜等待,看看是誰先冒頭,然後聯手給按下去。
其余地方上的勛貴們,自然都各自前往都督府轄地準備。
勛貴們這麽些年來,除了混吃等死外,也都是各交了不少的酒肉朋友,勢力同樣不小。
真玩起來,有皇帝當靠山,還真是不怕。
只不過朱由校這次的兩道聖旨,委實是讓全天下的文武官員們都是心驚膽顫了壹番。
顯而易見,皇帝這是要對衛所動手了。
雖說眼下還僅限於山西,可郭培民的動作,其余地方的文官、武將也都盯著。
他們同樣知道,勛貴集團不可能放任郭培民在山西的整頓行動就被這麽抵制下去。
雙方壹旦交手,這亂子可就大了。
話說回來,兵部這次出的事兒可真是完全令人沒有預料到。
以往出了事,大家夥的靠山都是朝廷的六部重臣。
現在可倒好,朝廷裏的那些靠山,要麽被皇帝嚇住,還在觀望,要麽就是如戶部尚書趙秉忠那樣,直接站到皇帝那頭去了。
在這樣的情況下,地方勢力想要反對這次朝廷降低軍屯稅,可就不是那麽好做了。
至於說朝中阻力的問題,更是不可能有了。
掌管這件事的兵部自己都怕得要死,甩包袱似的把衛所屯政壹股腦還給五軍都督府。
讓他們出言反對,比登天還難。
如果說讓朝廷對衛所的改革破產,只有壹個可能,就是武定候郭培民把事情搞砸。
現在,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郭培民的身上,期待他是個只靠祖上戰功蔭福的無能之輩。
可惜事與願違,郭培民恰恰是眾多勛貴中少見那個有誌氣的,這麽大的擔子落在肩上,只覺是恢復祖上榮光的時刻到了。
朱由校發旨的當天,郭培民帶著人就奔往山西,壹到鎮西衛,直接大刀闊斧的開始查屯政。
這可把當地衛所的文官武將嚇壞了,雖說指揮使於偉已經死了,可他們這些人還活著。
讓武定候這麽查下去,遲早都要查到自己的頭上。
……
鎮西衛城,壹群人正聚在壹起商議。
這裏的人,都是當地的掌權者,這次武定候郭培民下來,侵損的是他們所有人的利益。
以往官場相爭的這些人,也是臨時站到了壹起,因為所有人都知道,朝廷這次是要動真格的。
“郭培民已經在都督府衙門待三天了,鎮西衛的屯政再多,也經不起這麽查!”
指揮僉事說道,憤恨地喝了壹口酒。
岢嵐州的知州眼珠壹轉,也是說道:
“妳們說,這武定候如此囂張,簡直是不將我們在座的各位放在眼裏,會不會是有陛下撐腰?”
壹名千總嗤笑壹聲,道:
“武定候?屁!”
“也就是命好,生了個好人家,帶兵他會個der?指揮作戰,老子能甩他十八條街!”
眾多衛所武將也是不服,紛紛說道。
“於指揮使死的冤屈,多年兢兢業業,忠君報國,居然換來此等的下場!”
“朝廷居然縱容此舉,就不怕令天下間的武人心寒嗎?”
“我們這種地方,朝廷連管都不會管!”壹名副總兵冷笑壹聲,看了壹眼周身的武將們,自嘲道:
“當今陛下即位以後,九邊各鎮,就連山東的欠餉,都陸續補齊了,嶄新的盔甲、軍械,那是年年都有。”
“我們呢?我們多年為朝廷守衛內地,換來了什麽?”
“整頓衛所?說的好聽,就是想拿回弟兄們手上的兵權,交給那些什麽也不會的勛貴!”
“砰!”壹名遊擊猛然間拍案而起,抽出刀按在桌上,“嗎了個巴子,要我把兵權交給那些勛貴,癡人說夢!”
“這麽多年下來,老子的兵都是自己養的,沒花朝廷壹錢銀子,現在壹句話就想拿走?搞笑!”
文官們看著義憤填膺的衛所武將,個個都是露出了笑容。
定國公徐希臯這是在向英國公張維賢讓位,其實想想也能理解,畢竟這種領頭的,爭起來全無好處。
誰知道這次整頓衛所,最後會是個什麽結果,留條退路總還是好的。
何況來說,英國公壹脈,也是天啟皇帝欽定的南北勛貴領袖,去爭這個,不是等同於和他老人家作對嗎?
和皇帝作對,下場肯定不怎麽樣。
張維賢在心裏還是松了口氣,眼下這個時候爭頭壹把交椅,只會推遲行動的速度。
既然說定下了整頓衛所,最好就要立刻下手,遲則生變!
定國公都已經發話,余的勛貴們就更沒什麽好爭的,紛紛落座,廳中的聲音也逐漸安靜下來。
過了壹會兒,大家都不約而同看向前面,等著英國公發話。
“陛下托付重任於本公,我甚為惶恐,不過皇命在前,也由不得再如老夫人壹半拖延了。”
“鎮西衛屬右軍都督府管轄,兵部還政後,軍屯事務也要交接,如今掌印的是誰?”
聞言,眾勛貴嗡嗡壹陣,走出壹人。
這人穿著合身的常服,抱拳說道:
“在下武定候郭培民,萬歷三十七年時襲爵,現掌右軍都督府官印,還請英國公吩咐!”
張維賢上下打量壹番,見他頗有壹番英武之氣,驚訝說道:
“武定候?郭英將軍的後嗣?”
“先祖正是營國公郭英!”郭培民垂目說道,話語中有壹絲難以察覺的自傲。
郭英,傳說中的淮西十二將之壹。
早先擔任朱元璋親衛,而後被委任外出領兵,協助徐達、常遇春攻打陳友諒、張士誠。
洪武建國後,郭英開始擔任主帥,率明軍先後平定中原、雲南等地,身經百戰,重傷十七處,立下赫赫戰功。
洪武十七年,因功被朱元璋封為武定侯。
永樂元年,郭英壽終正寢,朱棣追贈營國公,賜謚“威襄”,許子孫世襲武定候爵祿。
郭氏壹脈,乃是正兒八經當年跟著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勛貴集團後裔,土木堡以後,留下來的淮西勛貴可是不多了。
正因如此,郭培民在在壹眾勛貴當中的地位極高。
張維賢驚訝的原因,是因為掌管右軍都督府的居然是郭培民,這樣壹來,鎮西衛的阻力能小不少。
郭培民這個人,他多少知道。
萬歷三十七年襲爵,今年三十壹歲的年紀,卻不是那些混吃等死的無能之輩。
郭培民,能耐如何尚且不論,但看他多年來的做派,多少帶有些先祖之風。
這樣的人下去打點鎮西衛,也能令人放心。
勛貴們在京商議了小半天,最後決定,動作不宜過大。
其余地方掌管各都督府的勛貴們,暫且如常行事,只有武定候郭培民,要去到山西,從鎮西衛開始,幹點大事。
畢竟這次的事是由鎮西衛開始,既然說兵部已經還政於都督府,那右軍都督府那壹塊,就需要郭培民去搞了。
郭培民在山西的動靜,肯定是會遭到反對的,這次勛貴們商量的目的就在這。
他們已經擰成壹團,接下來就需要靜靜等待,看看是誰先冒頭,然後聯手給按下去。
其余地方上的勛貴們,自然都各自前往都督府轄地準備。
勛貴們這麽些年來,除了混吃等死外,也都是各交了不少的酒肉朋友,勢力同樣不小。
真玩起來,有皇帝當靠山,還真是不怕。
只不過朱由校這次的兩道聖旨,委實是讓全天下的文武官員們都是心驚膽顫了壹番。
顯而易見,皇帝這是要對衛所動手了。
雖說眼下還僅限於山西,可郭培民的動作,其余地方的文官、武將也都盯著。
他們同樣知道,勛貴集團不可能放任郭培民在山西的整頓行動就被這麽抵制下去。
雙方壹旦交手,這亂子可就大了。
話說回來,兵部這次出的事兒可真是完全令人沒有預料到。
以往出了事,大家夥的靠山都是朝廷的六部重臣。
現在可倒好,朝廷裏的那些靠山,要麽被皇帝嚇住,還在觀望,要麽就是如戶部尚書趙秉忠那樣,直接站到皇帝那頭去了。
在這樣的情況下,地方勢力想要反對這次朝廷降低軍屯稅,可就不是那麽好做了。
至於說朝中阻力的問題,更是不可能有了。
掌管這件事的兵部自己都怕得要死,甩包袱似的把衛所屯政壹股腦還給五軍都督府。
讓他們出言反對,比登天還難。
如果說讓朝廷對衛所的改革破產,只有壹個可能,就是武定候郭培民把事情搞砸。
現在,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郭培民的身上,期待他是個只靠祖上戰功蔭福的無能之輩。
可惜事與願違,郭培民恰恰是眾多勛貴中少見那個有誌氣的,這麽大的擔子落在肩上,只覺是恢復祖上榮光的時刻到了。
朱由校發旨的當天,郭培民帶著人就奔往山西,壹到鎮西衛,直接大刀闊斧的開始查屯政。
這可把當地衛所的文官武將嚇壞了,雖說指揮使於偉已經死了,可他們這些人還活著。
讓武定候這麽查下去,遲早都要查到自己的頭上。
……
鎮西衛城,壹群人正聚在壹起商議。
這裏的人,都是當地的掌權者,這次武定候郭培民下來,侵損的是他們所有人的利益。
以往官場相爭的這些人,也是臨時站到了壹起,因為所有人都知道,朝廷這次是要動真格的。
“郭培民已經在都督府衙門待三天了,鎮西衛的屯政再多,也經不起這麽查!”
指揮僉事說道,憤恨地喝了壹口酒。
岢嵐州的知州眼珠壹轉,也是說道:
“妳們說,這武定候如此囂張,簡直是不將我們在座的各位放在眼裏,會不會是有陛下撐腰?”
壹名千總嗤笑壹聲,道:
“武定候?屁!”
“也就是命好,生了個好人家,帶兵他會個der?指揮作戰,老子能甩他十八條街!”
眾多衛所武將也是不服,紛紛說道。
“於指揮使死的冤屈,多年兢兢業業,忠君報國,居然換來此等的下場!”
“朝廷居然縱容此舉,就不怕令天下間的武人心寒嗎?”
“我們這種地方,朝廷連管都不會管!”壹名副總兵冷笑壹聲,看了壹眼周身的武將們,自嘲道:
“當今陛下即位以後,九邊各鎮,就連山東的欠餉,都陸續補齊了,嶄新的盔甲、軍械,那是年年都有。”
“我們呢?我們多年為朝廷守衛內地,換來了什麽?”
“整頓衛所?說的好聽,就是想拿回弟兄們手上的兵權,交給那些什麽也不會的勛貴!”
“砰!”壹名遊擊猛然間拍案而起,抽出刀按在桌上,“嗎了個巴子,要我把兵權交給那些勛貴,癡人說夢!”
“這麽多年下來,老子的兵都是自己養的,沒花朝廷壹錢銀子,現在壹句話就想拿走?搞笑!”
文官們看著義憤填膺的衛所武將,個個都是露出了笑容。